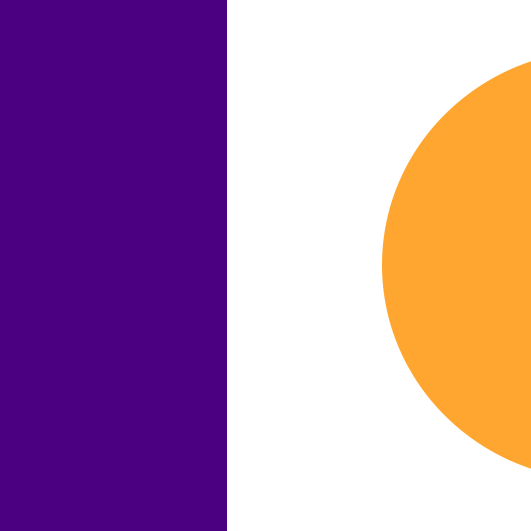出阿勒泰市,西行经阿拉哈克,继至布尔津。转道西北,行至哈巴河县境;经那仁牧场,可至喀纳斯。此路胜景在目,云开天朗,苍隼游空。尘世万象,宛在丹青,而众生尽为画中矣。苏瑶一行,是循此线,其时,将近那仁。
风渐从草中起,一层压着一层来,一阵一阵,透穿窗口,向人生扑。
“喂!你看到了,风在撩我的发”。林昭愿的半个身子探出了窗,咧嘴狂笑;车子迎风驰行,道旁的草木映照出风的模样,是不断翻涌的绿色波涛,沁满了一早泉水的清凉。
“我看到了!感觉是飘在风里。”陈最实与林昭愿同坐后排,大声附和着。两人将上身侧出车外时,车子便有了浆、有了翅,在风浪里颠。
“这风,比水还活。” 林昭愿将手伸出窗外张开,又收回来,拍拍脸,以此确认这是真的。恰好,道边有头牛,似在看她,她顺道唤了起来,“啊!快跑啊!牛!”
快跑?风在奔,草在涌,或许她唤的那头牛将她视为闯入者,但又觉她过于异常,故而呆立茫然无措,很是不解,快跑?如何谈起呢。
陈最实偏头看向随风忘形的林昭愿,大声喊着:“哎!你知道吗,你现在的样子像极了越狱的在逃犯!”
“是吗?他们都说北疆之北是阿勒泰,是山野的风,是狂野的梦。”林昭愿向风里大喊去。
苏瑶和丁酉是在前排的,他们生于斯长于斯,面对窗外的风光,在神情上并不显得夸张。先开口的并不是苏瑶,丁酉接茬说:“真的是越狱吗,这有什么好看的,不过是山,是草,是再普通不过的草原而已,算不得有什么特别。”
“看风景嘛,就如你在祈祷,我在舞蹈,不在路途和终点,在一种感觉。”陈最实看着丁酉开心的回应着,眼里戒备稍藏。
丁酉扭头认真打量起了陈最实,三十五岁左右的样子,脸偏长,轮廓清楚,颧骨不高,线条却硬,身子微侧还算放松,穿着深灰短袖。头发被风压得些乱,眉眼间神色算稳。
“那您是南方人?”丁酉道。
“哎,你这人眼真毒,那您是什么人,坐在小苏的副驾?”陈最实哏道。
有时候,目的和过程并不一定是趋向人心的真相,也许感觉才是。
“丁酉和我,家里是世交,在坐的各位是我最为关注的人,小到一餐一饭,大到身心舒畅,都令我万分牵挂。”苏瑶见丁酉并未接话,如是说。
待闲聊之余,车子行速逐渐趋缓,不得已将要停下,是前方有羊群浩荡着要横过路面,事发地正在两丘之间。
“那只黑山羊好凶啊,看到了吗?”林昭愿看向前方站在到中央、正对着车的羊,说。
“它对我们有敌意,莫要冲将过来。这车,前盖子挺薄的,受得住嘛?”陈最实观察这羊,体头比之寻常大得很多,两只眼睛格外黑,纵使额前浓郁翻卷的黑羊毛,亦难掩其眼珠满着冷意的黑亮,额上的犄角硕大如盘,昂头傲立若个将军。禁止向前的意味不言自明。
“这是野盘羊,不过黑色这种,是少见的。大家不要下车,等羊群过去我们再赶路。”丁酉跟道。
“我们再等等哦,野山羊的脾性不会太好,会耽搁一刻钟的样子。”苏瑶微笑着看向后排的陈林两人。
“估摸野盘羊的意思,不会这么轻易放将过去,这不像是过路,是堵路的。”陈最实补充道。
“有没有别的路呢,可以绕一绕,现在九点了,抵过两小时,天色就黑下来了,这条路上也就这一辆车,夜路总归是不好走的。”林昭愿没了之前肆意,开始盘算。
道上,羊群晃晃踱行,两丘碍住了视野,无法确悉它们数量。“这里信号很弱啊,要怎么办?”林昭愿示着手机屏,摆手道。
“是,这条路风光好些,只是少有人走,贯来只有二代网络,不用担心。”说着,苏瑶从包里拿出卷轴地图,徐徐展了开来,发现里面还夹着泛黄且沾带土渍的羊皮,羊皮上面布着错杂的线条笔画,瞬时吸引了四人目光。
“这是,羊皮地图。”林昭愿第一个喊了起来。“不会是寻宝图吧。”
“不是,这是我爷爷用的地图,第一次出门,他怕我走错了路,特意叫我过去,亲手交给我,说现代很发达,羊皮用不到,但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符、平安符。他年轻时候,很多次的翻山越岭、放牧赶场,是用这张图,祖上传下来的。特意嘱咐我一定得带着。”苏瑶一字一字说,从每个字的音调语气可以听出她对自己爷爷的亲切。
陈最实耐不住兴趣,拿过羊皮图端看。苏瑶则仔细看着现代的地图,丁酉凑了过去,看到图上车停处,道在两丘之间,是名河中丘,为牛羊南北迁徙必经的地方。
“河中丘,这是现在的位置,去那仁必须从这条道过。”丁酉说着,目光移向了四周,扫到车子左侧一条若隐若现的土路。顿了顿,继续说,“而且一路过来也没有什么小道,地图也没有显示。”
“那可不见得,你看。”陈最实将羊皮图展在车中,指向绕河中丘左,西偏北的一条路线——清远道。“我们可以绕行此道,直抵那仁,何必白白等着。”说着看向了苏瑶,“是吧,小苏。”
未待苏瑶答话,林昭愿已抢道,“对呀,你看羊皮图上标记的很清晰,而且你看左边,就是那条路,痕迹清晰得很。”
“要不,等等吧,万一发生意外,不好处理。”苏瑶眉皱轻轻,说着。
丁酉看出苏瑶的为难,解围道,“这张图太旧了,几十年前的老图,安全第一啊,况且不多久就到了,不必改道。”
“说来说去,你不就是怕出意外吗?”陈最实看出了丁酉的反驳,语气重了重继续说,“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意外里,无非是风险大小的事情。这种事有多大风险呢?难道等着、等着,风险就会自然消退?”
丁酉听着,脸色逐渐冷了起来,右手不自觉地揉摸胡渣,慢慢地看向苏瑶。心想陈林两人事儿可真多,快乐他们享有,风险倒让苏瑶承担,她只是小姑娘罢了。
车内氛围渐闷了起来,太阳已挂西边,凉意反倒不再升腾。“你不怕我们给差评呐?”林昭愿说,“还是第一次见羊皮图,照着上面走走怎么了,又不远。再说了,你丁酉又不是小苏,不是旅行社的人,你凭什么替我们做决定。”
此时,苏瑶意识到他们情绪的不对,但她知道相比走那条路,可能避免四人矛盾冲突的爆发,才是当下的紧要事。因而,心生一计,从口袋轻取出一枚铜色硬币,“既然有不同的意见,就抛硬币,让上天决定吧。硬币正面就走这条路,反面就走古道。”
陈林两人皆作同意,丁酉默认。我们该如何做以决断,我们该如何待以运气,该如何以他者的视角看事里事外。硬币从苏瑶拇指上轻轻跃起,升腾,翻转,跌落,是反面,落在了羊皮图。
此时,已过两刻钟,羊群还在过道,黑盘羊没有动过,以致令丁酉怀疑它是石刻的,还是妖物的。太阳挂在西边,山塬生出跃动的灰,看起来,倒显诡异。苏瑶发动车子,远远绕过黑盘羊,从古道驶去,在丘侧时,丁酉和苏瑶换了位置。古道年久多有坑洼,丁酉的车技并不显得比苏瑶好。陈林两人觉得颠簸,换去前排,车子由陈握持,依清远道行,一路霞光抖动,风景甚佳。
壹次修正於乙巳年九月廿三
於 鵉春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