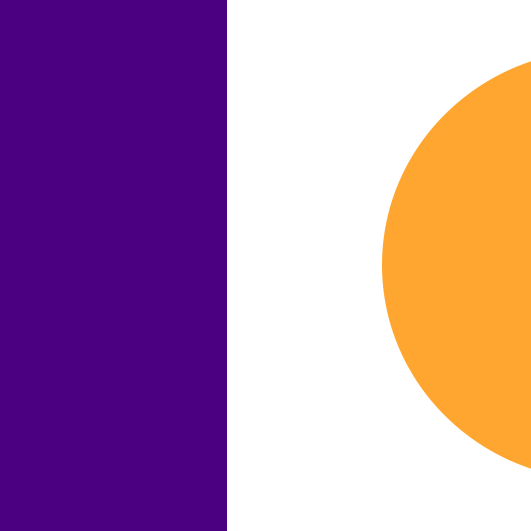只是觉得,在苍茫中,人何尝不是天地山野的景物呢,彼此互为照镜。时间恒定了生命的宿径,早晨中午夜晚,太阳月光星空,生老病死,是皆有的定律;却未得开渡灵魂的业缘,狂风暴雨炙热,向往嫉妒怨恨,贪嗔痴傲,为无常的困楚。人从景,会看暮色迷眼,会在余晖流连,陶醉徘徊,落日草原递了温情,上了眉间;景从人,会听人声冷颤,会见人影尾随,踌躇不措,食色男女遗了暧昧,热向心头。
观景、看人,许是心照不宣,为彼此停留。古道上可以看到苏瑶一行,车子停在路,他们亦没在车,反是四散探看。易道后,先是破了车胎,后又引擎故障。时下,位于羊皮图显示的弥台盆地中,不远处有溪水池塘。好消息是,苏瑶临行前带齐了指南针、帐篷、火具;坏消息是,手机讯号丢失,没带足够的食物,羊皮图存有误差。
暮色渐沉,西边天地接际的地方只剩一缝光亮。陈最实食指中指之间夹着一支香烟,小碎步不断,绕了四五大圈,停在离水塘稍远的小坡上。丁酉坐在塘边小石,小腿半蜷,两手搭在膝盖,塘里水清鱼小,些许水草,葱郁高拙。陈最实看向丁酉这边,张着嘴,似是要喊什么,微微地,声音没有吐露出来。于是,自顾地嘬了口烟,走往车边的帐篷行李,摆弄着,在解绳子。
“呐噫,让你委屈了。”苏瑶的一双白的小鞋轻轻踩在较大的石子上,悄悄踱去丁酉的左后方,说着,缓缓伸手递给丁酉一包速食,捎出一袭明如弦月的腕。她着了素色长裙,烟柳衫,似蝴蝶栖落白牡丹,蹲在丁酉旁边。
“怎么会,没事。”高音、温吞、清晰、缓慢,自带着开朗,这是苏瑶的声音,当听到“呐噫”时,丁酉心中已有了她的样子,扭头过去,目光从塘面移向苏瑶,看瀑墨的长发、灵气含锐的眼,及娇嫩却稍显倔意的唇吻,复道,“没事的。”
飞光、飞光,天光摧到夜光推。
“不见面的时间,七年是有了的。”苏瑶将下额抵在小臂,笑看着丁酉。
丁酉半转了身,斜对着她,眼里一半是她一半连向岸塘。丁酉看着有些呆滞,尽力拉起脸上肌肉,笑意泛在胡子拉碴的脸上,眼神逐渐正对她,“毕业,工作。你这事,可费心神的。”
苏瑶盯看他,向前挪挪身位,指着水塘说,“你看,我像不像打捞情绪的渔民……”苏瑶看着丁酉的侧脸,“记得吗?”
“嗯。”丁酉想到了,是他在学时写的小故事,说有一个海底的鲸鱼种群,怪诞的是鲸鱼的肉体如潜艇一样生硬,鲸鱼的灵魂除了幼年和老年是无法驾驭这个躯体的,但他们会灵魂出窍的法术,会寄生在鱼类的鳞间,并用情绪控制它们,随洋流四里漂泊,吸收灵气,直到老死时候。被寄生的鱼类叫做情绪鱼,是众生觊觎的,难得药材。
“现在,你就是鲸鱼。”他发不出声,像有东西梗在喉咙。草间萤火逐飘升,映在水塘星光点点。苏瑶摸摸口袋硬币,将它贴在右手掌心,站了起来,呈八字步,侧在丁酉旁边,一半是丁酉一半是水塘荧光。“如意如意,称我心意。”说时,苏瑶煞有介事,轻舞臂腕,纤细玉指舞了起来,食指和中指并拢,直如剑,无名指和小拇指弯向掌心,曲如钩,拇指类弓。“心归天宁,意归吾指,托于风水之间,易向潜渊之变。走!” 说时,控制不住笑了起来,一刹指丁酉,一刹指天,一刹指水塘,硬币瞬时向水面落下。
“女祭司,嗨呀,这几年你都学了啥东西。”丁酉看着苏瑶比划,一时分不清哪是哪,却咧嘴笑了起来。说时,一条雪色白鱼跃起,衔币入水,煞时无踪,只留水波荡着。
“啊,快看!是鱼,这是我的法术!”苏瑶见池鱼跃水,开心极了,笑声如同银铃一般。“怎么会这么巧,你的厄运到头了,剩下的都是好运呐。”
“托你的福,祭司。”丁酉说,夜幕究竟没盖住他的笑意。
“临水诀,在《金陵神仙录》看到着,讨个好彩头啊!”苏瑶看着丁酉,亦是开心。“艰难苦恨、潦倒新停,你怎么杭州扮起了草堂的角嘞。”
苏瑶稍作停顿,像眼前萤火探知黑暗一般,不露声色地感受着,丁酉的笑意并未消失。于是接道,“冥冥之中……”
“你还说我,你看看,你这个受气包,别人的话这听那也听,这也做那也做。趁早换件差事干。”丁酉稍作沉默,不想场面突冷,接着说。
“哎,行!”“那带着我干呗。”
丁酉露出了笑意,却是有点苦的。不觉中,夜色如倾倒的墨,涂了眼前一黑。少年相识的人也是一见如故,即有生疏,彼此也看得真切。
“光说话不饿呀!”是林昭愿。她拎起兔子在丁酉和苏瑶面前晃了晃,将枯木枝哐当扔在丁酉边。苏瑶一时愣住,要接话时,林昭愿已转身,于是抱着柴火跟去。
小坡上,陈最实正在搭帐篷,总在刚要搭好时就塌了下去。只得喊人。“丁酉!你来看,撑杆有问题。”
丁酉闻声来,接过陈手里的撑杆,掂了掂,又察接口。“卡榫反了。”随手一扭一接,两人便将帐篷搭了起来。陈最实“嗯”了一声。
人总有不擅长的,比如说,良夜要有篝火,篝火要有吃食,这方是一种夜的意趣。而孤独与喧闹,就像镜子的两面,是需要猜的,就像湖面下的鱼,要引诱的。
所以他们谈起了自己的过往,林是家中无趣,随大流;陈是律师。
“小苏呢?”林问道,“怎么想做这个呢。”
“投简历来的。”苏瑶应着,见林昭愿还看她,补言说,“毕业了,总得找点事做。家里觉得工作近点好。”
“哦?”林抱着膝盖,“这次意外,小陈和小苏,得负主要责任。看旧图,抛硬币,荒唐!”
陈没有反驳,苦笑道:“是我冒失了?”心想,当时看就你喊最欢,真是甩锅的一把好手。
苏瑶低了低头说,“对不起,我当时……只是不想大家再争执下去。”
“行了,过去的事有什么好争的。今天好好睡一觉,明天赶路才是正经事。”丁酉本发着呆,还是补了句。毕竟,情愿与否,都会梦到夜深处。
壹次修正於乙巳年十月二十
於 鵉春